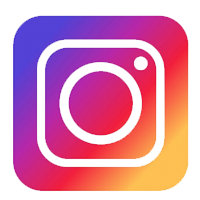在普洱茶的邊緣行走—攸樂山
我上的第一坐山,是攸樂山,基諾族居住地,我習慣稱它基諾山。
基諾的意思是“跟在舅舅後邊”。由這個名字,可見基諾人曾經經歷過漫長的母系社會時代。基諾人無自己的文字,亦無固定的姓,兒子的名的第一個字取其父名的最後一個字。以我的朋友胡不歸為例:胡不歸,兒子就叫歸去來,孫子叫來新雨,重孫叫雨中荷,再重孫叫荷香普洱茶??????
基諾族的這種稱名方式,在雲南並不是唯一的,還有許多民族也是這樣。如愛伲族,父親叫某某且,兩個兒子,一個叫且大,一個叫且二。
其實,古代華夏民族也常常用這種稱名方式,如今天的林姓、施姓、高姓、遊姓,都是以先祖的名字為姓。不過雲南一些少數民族的姓氏也慢慢固定下來,如且大且二,他們的孩子今天都以且為姓了,而不是叫大某某二某某。
基諾人沒有自己的文字,但據我們的基諾朋友山二說,他們曾經是有文字的,他們的祖先用他們的文字將他們的歷史寫在牛皮上。後輩兒孫有一年遭遇饑荒,沒辦法,將牛皮煮來吃了,結果,他們的歷史和記載歷史的文字也被一起吃下去了。山二為此深感遺憾。好在是吃下去了,雖然沒有了文字,但是都記在心裏,可以口述歷史。
在六大茶山中,基諾山的生態環境是保存較好的。基諾人很團結,他們頑強的守護著自己的山林,拒絕外來力量的進入。在已知的歷史中,基諾山從來沒有被一種外來力量所攻破。不過,這幾年還是有了一些變化,原來(04年),在基諾山範圍內基本不種橡膠樹,現在也種了不少了;原來經過基諾鄉中學繼續往上走,沿路的大樹很多很多,一年一年下來,也明顯的稀疏了。
我們去的基諾寨子是亞諾,他們原來是居住在西南面的司土老寨,1974年才在政府的安排下遷來這裏。這裏的老茶樹在他們遷來之前就有,是什麼人種下的不知道,他們遷來後就屬於他們的了。
我很喜歡基諾人,尤其喜歡師弟與他們的親密關係。
那天我們進寨,車剛在木樓前停下,主人山二和他妻子阿眉(音)就迎了出來。阿眉快步走在前面,張開雙臂將師弟緊緊摟住,她的頭貼在師弟的胸前,高興的說:好想你呀!師弟也摟著她,輕輕拍著她的背,旁邊,是滿面笑容的山二。那種天然,淳樸和真摯,叫人真的很感動。
還有,就是他們的坦蕩。今年春天,我們剛到山二家,同寨的阿檦(音標)就過來了,他手上拎著約三公斤毛茶,對師弟說:今年我的大樹茶不給你了。師弟問為什麼,阿檦說:今年某某茶商把我的茶全包了,大樹小樹混收。你只收大樹茶,所以我答應了他們,明年他們不收了,我再給你。說完,他將手中的茶遞給師弟,又說:這點大樹茶,送給你喝,頭春的。師弟高興的接過茶,連說沒關係沒關係,理解理解。阿檦的小樹多,有人混收,好賣些。這就是他們的處事方式,有什麼話,直說。
基諾山的茶好喝,當然,我說的都是大樹茶。具體什麼感覺我不會說,不會描述,只知道好,怎麼個好法說不出來。不僅對基諾山的茶說不出來,對所有好茶也都說不出來,即使經歷了這麼些年,喝過無數種茶,還是這樣。有時看到一些朋友那麼細緻的談他們品某茶時的感覺,我真是很慚愧,可能我一是對茶沒悟性,二是對普洱茶從來不上心吧。這裏順帶說一下,許多朋友談茶的帖子我都沒去跟帖,還望大家體諒,因為實在是一具體談茶,我就傻了。
基諾人基本不與外族通婚,但是他們並不排斥外族人,有不少外族人常年在基諾山居住和稚N液蛶煹茌^為熟悉的,就有三個四川人,他們的年齡都在四十歲以上,一個是木匠,一個是泥瓦匠,一個是剃頭匠,來這裏稚加锌於炅恕>驼f說這三個人吧。
木匠是一個人來的,手藝極差,剛開始還能攬到一點活,後來就不行了,沒人請他,不得不靠幫山民幹農活打短工為生。有時無工可打,便連落腳的地方也沒有了,好心的山二便常常收留他,讓他白吃白住。去年總算有了著落,到另外一個寨子當了上門女婿,和一個寡婦一起過日子,聽說過得還好。
剃頭匠也是一個人來的,在基諾鄉的街上擺個剃頭挑子,手藝可以,會刮臉,理次發三塊,不富裕,但過得下去。師弟每年找他理髮兩次,喜歡他刮臉時的舒服感覺;我不,嫌髒。
泥瓦匠是一家三口都在這裏。泥瓦匠雖說是與泥瓦打交道,但平時卻是衣著整潔,雖說已經過四十了,仍可看出他年輕時的英俊。他手藝好,這些年基諾寨子蓋的新房,大多是他主持的。他收費不高,吃住在主人家,每月還能落個一兩千塊,說起來,在三個四川人中是最能掙錢的。不過他老婆既凶且悍,他掙的錢每次都被搜的一乾二淨,他又不敢反抗,結果,身上常常拿不出一包煙錢。有時與老鄉剃頭匠相遇,常常腆著臉找剃頭匠要煙抽,當然,也免不了被剃頭匠善意的奚落兩句。我見過他老婆,實在是不敢恭維。這三個四川人,想想,唉,一個人是一個人的命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