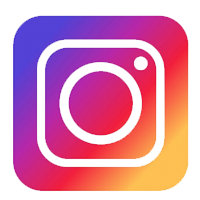倚邦古茶山-雲南大葉種的異類
大佛爺的茶,與眾不同。
茶氣洶湧,奇香,極苦,然瞬間回甘,如驚濤拍浪。
他說,這是自己做的。
本地茶,春茶,野茶。
看葉底,碩大無朋,葉脈崢嶸。
雨,不知什麼時候停了,天地間,再次敞亮開來,金色浮屠的光彩,映照著雨後的碧綠,分外生動。
緬寺周圍,大片的茶樹和菩提樹結伴而生。仔細打量,樹的根部粗大,至少有數百年的壽命了。
各色各樣的花,在初夏微雨中,開得爛漫,有曼陀羅,但更多的叫不上名。置身此地,內心再冰冷粗糙的人,都會變得溫潤細膩。
我們所在的村寨,距緬甸很近,僅兩公里之遙,抬腳即可過去。在茂密的原始綠色中,潛藏著很多野茶樹,沒有主人,誰采下來就是誰的。
布朗族,是璞人的後代,老祖宗種下福田,蔭庇子孫。他們都信奉小乘佛教,都喜歡茶。
一片茶葉,幾響梵音。融為一體。
人的世界,神的世界,始得相通。
兩口大鐵鍋,端坐灶台,肅穆神聖。旁邊是曬青用的竹篾。
大佛爺說,茶,從來沒有離開過佛家的生活,尤其是雲南普洱茶,和佛教有著很深的淵源。
大量普洱茶曾被叩轿鞑兀瑢?嫿ǚ鸺揖?⒔塘x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。這,大家都知道。可大家不知道的是,小乘佛教的弟子也喜歡喝普洱茶。
此時,小僧恰好換茶。
大佛爺斜看一眼,說這是甜茶。
一種不容置疑的語氣。
帶著幾分疑惑,我們入口品啜,果不其然。
茶已經完全融入生活,看上去不動聲色的敘說,卻是一種超拔的自信,或者說習以為常了。
大佛爺根本無需表演。
放棄聲色奢綺,為何獨獨對茶保持如此濃厚的興趣?
這就是“癡”。
他說,雲南是普洱茶的故鄉,易武地區多產甜茶,為何?先民們也種過苦茶,只是大家喝不慣,就將其砍掉了。
布朗山的民族更包容些,不管什麼茶都能接受,這讓甜茶、苦茶、苦甜茶得以保留。這幾年因苦茶稀缺,身價百倍。
靠近緬甸的茶樹,樹齡都在300年以上,當地民眾沒有成功學的概念,在物質上追求甚低,不會廣植小樹,甚至有時候政府發的肥料,他們都倒掉,因為背一袋肥料翻山越嶺,累死人了。
古茶樹也不需施肥打藥,幾百年都過來了,體質較弱的,早就被淘汰掉了。每棵茶樹下,都有一層一尺多厚腐殖質,養花種草都是好土,營養足夠。自成的生態系統,數百年來哺育著布朗族人們。
寺廟為何要制茶呢?沒聽過。
大佛爺覺得這很正常。寺廟,也是為人的。寺廟,為何不能做茶呢?
小時候的記憶全是茶的故事,他嗅著茶香長大,眼裡、嘴裡,鼻子耳朵裡,全是茶的印象。即便修行,也保持著對茶的一種美好眷戀。
寺廟和茶,天生就有緣分,不可或缺。
過午不食,喝茶,可補充體內能量。
茶葉,在小小的佛寺中,有著超過金錢的感情。
可市場上買的茶葉,大佛爺總覺得遺憾,和他記憶中的味道不一樣。而自會制茶,懂得微妙所在,寺廟都被茶樹淹沒了,為何不能自己給自己做一點點呢?
寺廟所需茶並不多。
平時,他放空自己,參研做茶的精妙之所。
每年春茶季,專門留幾天時間實踐。
一杯好茶,最重要的是源頭和工藝。
別人送來的茶葉,他根本不放心。要讓每片葉子,找到最適合自己生命狀態的存在形式。
他親率眾弟子採摘。只要古樹茶,只要頭春鮮葉,大小均勻,葉片端正,他將苦茶、甜茶、苦甜茶分門別類出來,單獨制茶。
整個過程緩慢而專注,制茶的那幾天,他很少說話,整個人都癡癡的。
心無旁颍?涡臏Q慮,將一件事情做到極致。
這便是法眼。
太仔細,太認真。每天只能採摘十幾公斤鮮葉,全體僧眾恭恭敬敬抬入僧房。為找到童年的口味,他親自萎凋、殺青、揉撚和曬青,像做一場法事,一絲不苟。
此時,我的眼前浮現出一幅場景:
火燒的正旺,木材劈啪作響,一個光頭彎在灶台前,雙眼緊盯殺青鍋,兩隻手不住地上下抖動,昏黃的燈光下,映出大黃袈裟,和一張大汗淋漓的臉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