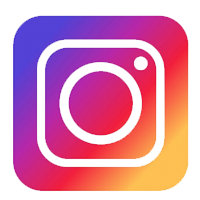“越人遗我剡溪茗,采得金芽烹金鼎。素瓷雪色飘沫香,何如诸仙琼蕊浆。一饮涤昏寐,情思朗爽满天地;再饮清我神,忽如飞雨洒清尘;三饮便得道,何须苦心破烦脑。此物清高世莫如,世人饮酒多自欺。悉看毕卓瓮间夜,笑向陶潜篱下时。崔侯啜之意不已,狂歌一曲惊人耳。孰知茶道全而真,惟有丹丘得如此。”
唐诗僧皎然的这首《饮茶歌诮崔石使君》,可谓关于“茶道”一词的最早记载。作为修行类茶道的代表人物,皎然的这首诗道出了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,超越人生,栖身物外,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。
今日看来,所谓得道成仙一说自然遥不可及,然而在沏茶、赏茶、品茶的过程中修身养性,学习礼法,思考人生,却不失为一种极好的和美仪式。喝茶能静心、静神,有助于陶冶情操,去除杂念。这种流传数千年的茶道精神便是茶文化的核心和灵魂。
在我看来,茶之道的精髓可以归结成清、雅、怡、和四个字。
清,是指“清洁”“清廉”“清静”“清寂”。品茶之所当清洁,所用茶具当清洁,煮茶之水当清洁,最关键的是,煮茶之人其心当清洁。因茶艺的真谛不仅要求事物外表之清,更需要心境清寂、宁静、明廉、知耻。故,非内心清纯之人难得其道。
古人品茶多选一曲径通幽之处,独自饮茶品茗,边喝茶边思考,以饮茶作为思考、参禅、修行的媒介。随着饮茶数量的增多,饮茶的感受从生理到心理再到心灵,完成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积累,最终达到“宠辱不惊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之境,使心灵得到完全的放松。
陶弘景在其《杂录》中说:“苦荼(茶),轻身换骨”;宋代范仲淹诗中:“众人之浊我可清,千日之醉我可醒。卢仝敢不歌,陆羽须作经。长安酒价减百万,成都药市无光浑。不如仙山一啜好,冷然便欲靠风飞。” 便是此种境界。明代主权的《茶谱》更是说“予以一瓯,足可通仙灵矣。”
雅,即茶之意境,把茶的内在精神体验用语言和艺术表现出来就是“雅”,而“雅”所蕴含的茶的无限真谛是需要“吃茶去”才能体验的。对于这一意境,从沏茶、奉茶、品茶过程中便可看出。
首先是观赏茶器及茶叶。此后煮水、沏茶、观茶色、嗅茶香、品味茶汤,每个步骤,无不渗透着“雅”的意境。水,要用窖藏的雪水或是甘冽的山泉;煮时要注意火候,一定不要等到三沸过后;要等待水温稍稍降下才可醒茶,头遭水要弃去,冲泡时要将水从高处冲入杯中;之后静待茶叶慢慢的舒展身躯,浮起,又落下;待无色的水被染上或青碧、或金黄、或微红的颜色时,心中自是别有一番欣赏;轻嗅茶香,让温暖湿润的馥郁之气融入肺腑;小口品着茶汤,让茶与心灵达到一种和谐完美,使人返璞归真。
这一行云流水般的过程,可不是非那谈举止斯文之人不能完成的么?
怡,即和悦、愉快之意。这一字道出的是茶道中茶人的身心享受。茶之道虽求“清”求“雅”,却并非高高在上,拘泥于一定的形式礼法,它亦可体现于平常的日常生活之中,即茶道中人那颗快乐的心。这一点,从古人的茶诗中可窥一二。
卢仝诗云:“柴门反关无俗客,纱帽笼头自煎吃。”“碧云引风吹不断,白茶浮光凝碗面”,一碗“喉吻润”,二碗“破孤闷”,“三碗搜枯肠,惟有文字五千卷”,“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平事,尽向毛孔散”,“五碗肌骨轻”,“六碗通仙灵”。从刚开始的解渴、疗愁,到后来的直抒胸臆,进而借汗水将愤郁之情尽皆散发,使心灵轻盈,最后,完成了肉体与心灵的彻底净化,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而如今,人们常邀二三知己,至一风光秀丽的茶棚中,听行云流水的古琴古筝,闻清香扑鼻的浮动茶香,看一泓清泉中落英辗转开阖,赏景饮茶。虽然没有达到如古人那般出神入化的境界,但至少在品茶闲聊的过程中增进了友谊,探讨了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话题,也得到了身心的愉悦。
和是中,和是度,和是宜,和是当,和是一切恰到好处,无过亦无不及。儒家对和的诠释,在茶事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春季龙井,冬季花茶,暖胃普洱,下火栀子,选茶当符合时令节气以及喝茶人的身体状况,方能养生而不伤身;品鉴香茗之地不宜喧闹嘈杂,亦不应死气沉沉;沏茶之水不宜太生,不宜过沸;品茗之盏不宜过大,不宜过小;冲泡次数不宜太少,不宜太多。关键的是,品茶人的心境更要平和,不可大喜大悲,大起大落。如此种种,可不正是儒家的不温不火,中庸之道么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