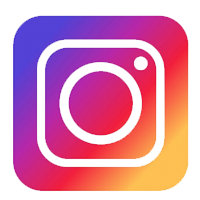��ɰ�����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ˆ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ξ���1506-1566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K���d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عż�ӛ�d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ɰˇ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Mʿ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ֿˌW��̖ȭʯ���e̖�Uɽ���ĕ�ͯ������δ�@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跽ʽ����赽�ݲ��׃��֮�H���ܮ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Dž��˵�Ӱ푼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W����ɮ�Ɖأ��K��ȡ�����չ��u���Y���õij��ͷ���ʹ�Ã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أ�ʹ��ɰ�����l�P���÷���ڡ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ٝ������녣�“Ó�քt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ұ�t�Y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׃�����컯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֮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”�ܸ����ڡ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Q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ӣ�”ꐾS�¡�ٛ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ˉض����Kϵ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“�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ʡ�J�ġ�Փ�ɽ^�䡷�t�f��“���d���֔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念��•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h�I���d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һ���m�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ʢ�費ʧԪ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䡢����īʿ�㲻ϧ�rُ֮��”��Ҋ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r�O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ԁ��Ďװ����e�˂�����䌚��“Ȼ������֮�r�أ������߱ر��ӣ�”������wɰ�؈D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ɴ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ؼ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hҲ�Ё��Ծã��ұ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һ�ǡ���Ŀǰ���ԣ��҂��б�Ҫ�����F�Ѳt����īIʷ������̽�����J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
һ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ˣ�
�����ᵽ�����Ĺż��īI�����S�μ���1549-1604���ġ����衷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Ѷ�ʮ���꣨159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Tע”�l�d��“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Օr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r�ˌ�ϧ���w���Դ�ɰ��֮����ȡɰ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Լ���Ԭ���(1568-1610))���S�P���r�С�ƪ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f�Ѷ�ʮ����(1598)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(1600)����녣�“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ȶ࣬Ȼ�ԅ��ˡ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ȷQ�y�ã��S�|��ā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”
�����^ԔՓ�������Ĺż��īI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ƪ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ܸ��𣨼s1599-1645���ġ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ʼ”���d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U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Uɽ�x����ɳ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춽o��֮Ͼ���`����ɮ�Ľ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Ѩ�У�ָ�Ӄ��⣬ָ�����[��ɰ���̥���۰����ʸ����ЬF������ҕ�Ա��档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Q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څǃ����Ҋ�r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t�̹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۾��A녡�…�r���……���Է¹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1619-1679)�ġ����d�N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“��ɽ��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СʷҲ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ɮʼ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ģ���r���䷨�t�֗�ģ��……���գ�‘ɮ�݄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A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һ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÷��(1631-1700)�ġ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ȭʯ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ɽ���yһ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أ��O����ɐۣ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Ǖr�Ӵ��֮��……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��档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f����ԢĿ���ܡ���С���Ԋ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^����֮��Ѩ��׃�߮W�Ԟ�ء�”
���ɹ����Ɖصģ��^�瑪�ǡ���wɰ�؈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37�꣩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f��“Ȼ�����Hһ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¹��Tʽ�����R‘����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С���ȷ��Uɽ����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ˡ�”����Ҫ��ԭ�_����ʷ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ˇՓ�ļ���<������ʷ>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}�飺���˕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зQ��“���طQ‘����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쳽(1508)�Ͻ�Ԫ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ƏV�ݲ��É���Y��֮‘���’Ҳ��Ω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‘��Ԫ��’֮���֣����r��Ұ�g���pҕ�‘�ٹ���ˇ’������Ӛ춺���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֮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ɮ������߅֮δ�г����С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‘����’�������‘����’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‘���һ’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‘����’һ�~֮���x���ɽ�‘��’��ָ‘��’����‘��’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ɢ�~��֮‘�ȴ�’��ؕ������”“���˵��`���Ǐ����ܵġ��仨Ԋ���е�‘���ʹ����ü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‘��’��‘��’��”��
���@�e�҂���֪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_�����ˣ�ֻ�nj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h��һ���J��һ���ٲ����µ�С��ͯ���ܾ�����ˇ��ʽ���̱�ʾ���ɣ��K�ƶ����ɕ�ͯ���˅���“����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“����”ֻ�lj�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˕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Ʌ��˱���睿�춉��ϵġ��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ă��c�Ќ����˕�ͯ�ƉK�]�з��J����Ҫ���J����˅��c�ˣ����ƣ��OӋ��睿̣��Լ�����֮ͯ���Ю��h����“�J����˅��c�����ƣ��OӋ��睿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ݲ��õ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䄓ʼ�c���˅��c�Լ��ܵ����r���˵�Ӱ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P�S�ģ���“����֮ͯ���Ю��h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c����(1797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h�f־����ĩ•�W�_��ӛ�d��“�Uɽ�f�W������鹫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ه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L���ǣ��뼮�����f�ѱ����Mʿ�����ꄷ������څǣ������e�ˣ��°�֪�h�����хǣ������e�ˣ�����֪ͬ��”���H�{�˗lӛ�d�ԟo���C���Ɖصĕ�ͯһ�������@λ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˵ĕ�ͯ�����Ў�λ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Пoʷ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҂�ֻ���f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“����”�lj��֮�f��ֵ����ȶ�������lj�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ў������Jͬ�Dž��˕�֮ͯ�������ѳɞ���˕�ͯ�Ĵ������ֻ�ԭ�����Dž��˕�ͯ�Ąe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Թų������⣬߀���֡�̖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e�Q�ȣ�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õķ�̖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ˁ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̖���e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ڛ]�д_��ʷ���C��֮ǰ�����˵ĕ�ͯ߀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Q֮���^���У����ȿ����Dž��˕�ͯ�Ąe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ԅ��˕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K�ж�N���ؽY���Ąe�Q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ڡ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У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U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”���㽭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(1650-1727)�ڡ����嶼��ע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ɽ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”�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684-�s1745���ఴ�����е��f���ڡ�̨ꖰ�ԁ��ע��“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U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ߡ�”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䛡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Uɽ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ϵԻ���£����Ԟ�澣��K�`����֮��”��֮��߀�����ˌ����q��ע����д��ɻ��J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ˣ��б�Ҫ���@һ���}�M�б����_�J��
�����҇��h�Z�~�Z��ጣ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һ�~��Ҫָ���N��
1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2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
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4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T��Ŀ֮һ��
5���ſh����
6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ɫ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µ��ˡ�
ǰ��N��ԓ�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“��ɫ����ɫ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µ���”����x�飺�h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b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ߵĴ��Q�����w��ָ��
(1)ָ�Ů����ͯ���h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˼�h�ţ���˼����”�ƷY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־•�S�hꖡ���“�h������ϰ�Ͷ�]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ȏd��Ҿ��녣�‘Ů�ɵ����Ρ�’”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С�f•��Ӿ��߫@�Q�ġ���“���^���g����Ҋһ����Сͯ���Mǰ��Ҿ��”��Ԭö���S�@ԊԒ�a�z�����壺“�t����Ԋ�߶࣬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١�”
(2)ָ��Ů���mŮ������κ�ܲ١��c̫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ˣ��L�����ҡ�”����ʷ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¡�Ů�ơ�Ů����Ůʳ���ɹ�Ůūҕ��Ʒ��”
(3)ָ�������帻��س硶�ྩ�q�rӛ•��̨����“�˽ǹ�������݅����Ū����'��質��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”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أ�“�ɰ����°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”
(4)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S־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“��ȡ���棬���P����֪���~��ʹ����֮��ȥ��”
���Ͽ�֪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ȿ�ָ�Ů��Q��Ů��Ҳ��ָ�̏ģ�ָ�S���ź�֮�ˣ���Q��ͯ����ͯ��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K���nj�ָ�Ů���̏ģ�Ҳ�����f“����”�ǂ��o�Ԅe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ڡ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ԓ�ǵ�λ���µĴ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ܴ_�����Ů߀�Ǵ�ͯ��Ҳ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ָ���ġ��mȻ�҂����ܴ_ָ�ܸ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”һ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÷���t���_��ָ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“Сʷ”����ָ���ġ���ͯ����÷�����Q“Сͯ”��ָ��ͯ)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Ю��h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wɰ�؈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N�f��һ�Dž�÷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녣�“……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ܲ��ߡ���ϵ��녣�“Ҋ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t�̹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۾��A�”�����Dž�鶿͡�����䛡�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ݸ�־��녣�“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……ʼ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ʯ𭡷녣�“���dɰ���…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Q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“÷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鶿ͼ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Ž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…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‘������’”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N�f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鶿͡�����䛡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ݸ�־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ȣ���鶿͡�����䛡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𡶉�ϵ����ԭ�ģ��H“ϵ”�c“�O”�в�e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ܸ���ע“Ҋ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t�̹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۾��A�”����䛣����q��ע�t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ɽ��ͯ”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ݸ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念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(1695)�̱�����ԓ־��ʮ��a녣�“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……ʼ춹���”���K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䡶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d�h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念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(1686)�ġ����d�h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һ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鶿ͼ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K��Փ“�DŽ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䌍�����猢“����”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ģ������S�μ��ڡ����衷(1597)�зQ��“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Լ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S�P���r�С�ƪ(1598—1600)�зQ��“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ȷQ�y��”����ˣ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r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Kע��“�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څǃ����Ҋ�r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t�̹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۾��A녡�”���@���ܸ����HҊ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ĕr���¹����،���ʷ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Р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҂��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ͬ����“��”���գ����^“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գ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�ӌO����“��”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“��”��ͬ“��”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ĩ����Ą���ڡ���ʯ𭡷���s1644��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Q����”��Ҳ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ܾã��ڱ����˂�ힵ��^���У����˰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ġ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ڽ�ɳ�W�Ɖأ�
���ܸ����ڡ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ɳ�£����f���g���W����ɮ�Ɖء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(1268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ڶ�ʮ���d��“�V����ɳ�UԺ���ڿh�|����ʮ�e�����ϣ�x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~‘���}��ɳ’��¡�d�Ľ��~��”��Αc���꡶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h�f־����ĩ�����^�d��“��ɳ�U�£��ڿh�|����ʮ�e�����ϣ�x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ĶU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~‘���}��ɳ’��¡�d����‘�V����ɳ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L�}��ڡ����Ğ��¡�”���н�ɳ���c���ϣ�x��ɽ����ʲ�N�P�S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ڶ�ʮ���d��“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U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ӡ�L�[���ɡ���̖��ꖶ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Uɽ䛡����F�ĘO��g����٣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ԓ־����ʮ���d��“�Uɽ���ڿh�|����ʮ���e���ϣ���[춴ˡ��^�|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U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ԁ��ӛ̨�ء�Ȫʯ����ľ֮�٣��d���Uɽ䛡���"��Ҋ���Uɽ�c��ɳ���mͬ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K����һ̎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ڶ�ʮ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ɳ�UԺ�����ϣ�x��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أ��@Ҳ�nj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`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Uɽ��ԭ�����ȣ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ġ���ꖶ���ɽ��ӛ����Ҋ���Ď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Ĵ⡷����ʮ�壩������녣�“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z�s춳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w֮�϶����E�ɡ��خ���ɽ֮ꖣ��|Ϫ֮�ϣ����^֮����価��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Uɽ��Ϫ����Ϫ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B����Ҳ��”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ƴ��K�ݸ��ˡ����W���ģ��ȹ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862-888)�r������ʰ�z������(888-904)�r�ٞ�o���У��ݑ������ɡ�ͬ�Е��T��ƽ���£���̫���َ��T���[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d����ɽ֮ꖣ�̖��ꖶ��ţ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ꖶ���ɽ��ӛ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f��ɽ����Αc����(1797)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h�f־����һ•����־•ɽ���Q��“��ɽ���ڿh���϶�ʮ�e���f���G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r���H�[��“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к���患����ھ�ɽ�����~��ɽ���|�ϣ������^“��ɽ֮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ϣ�[��ɽ�ּ��Uɽ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1070)�n�~��“���}��ɳ”�UԺ�c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�����(1129)���w��;����ɳ�UԺ�K�}�~춱ڣ�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īIӛ�d��ɳ�UԺ�����£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ᵽ�ϣ���Uɽ���ɵػ��һ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~����(1077-1148)�����䡶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ϣ�Ҋ���Ď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о͌��ϣ��ӛ“��ɽ”�`��“���ɽ”���K��“���ɽ”��“�Uɽ”��“��ɳ��”��“�ϣ��լ”���һ̎����Σ��c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H�P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ة���ܱش�(1126-1204)�ڡ������[ɽ䛡�(1167)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δ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患���Ϫ�И�̖���ɘ�……��ڽ�ɳ�¡����Uɽ���L�v��̨���Ý����AȪ����ϣ�z�EҲ�����Ў[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ʯ���~���ѡ�“�ܱش����H���[�[�����[ɽ䛡����f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ᣬ���Uɽ���P�I���@��“��”�֣����L�ϣ�z�E���f����ɳ�²�����Uɽ�ϣ�z�E��ֻ�����ڽ�ɳ�³����ɳ���c�Uɽ��ȫ�ǃɂ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һ�ٶ��꣬���r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Ҫ�Ǹ����Ǻ黯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÷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ղؼ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Ă��f�����f�Ѕ��˔y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|�ϵĶ���ɽ�e��Ժ̎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g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҅��˄e̖“�Uɽ”���K���С��Uɽ˽�塷ʮ�������˄e̖����Դ���ϣ����“�Uɽ”֮���⣩���@��Ȼ���c���ϣ�x��ɽ�����Uɽ���Լ���ɳ����һ���ɴ˂��飨���ܸ����Ɣ��飩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ɳ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ɳ�£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W�Ɖ�����ڽ�ɳ�¡����@�H�Ǹ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Ɣࡣ
�塢�����Ƿ��ڴ�ɽ�W�Ɖأ�
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ڡ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“�x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”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d�N��ӛ��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ɽ��ɮ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ɽ�W�Ɖء����÷���ڡ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Єt�f���ҵġ�����ȭʯ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y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Ɖأ������ǽ�ɳ��߀�Ǵ�ɽ���أ�
��Αc���꡶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h�f־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־•ɽ���d“��ɽ��һ����ɽ���ڿh�|����ʮ�e��”��ԓ־��ĩ•���^�d��“��Դ�U�£��ڿh�|����ʮ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Ԫ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ɮѩ�֜Q�ؽ������yʮ����ɮ�����ٽ���Ո�ԏU��“��Դ”�f�~��֮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~��”����ɽ�¾��ɳ�����ʮ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һ�����}�У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ɳ��߀δ�ص׳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ݺͅ�÷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ž�÷���ď��棩�҂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Dž�÷�����f“��ɽ“���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Uɽ˽�塷���Ў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磺���Uɽ˽�塷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Ԋ녣�“�����p�I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녡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£�����頖�֡�”��ͬ��һ�����ԡ�Ԋ녣�“С�[��ɽ�£��ƻ����M�֡�˪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ȽȽ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¶���]ϲ�O�K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Uɽ˽�塷������Ԫ�շ����Q���̶R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Uɽ����ӛ�¡�Ԋ��녣�“���ҷ�ԫ�l�K�{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ô��ٌ٣�˼����ɽʰ���ԡ�”����Ԋ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ɽ”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з��ᣬ�˷�������Dž���֮���Ǿ]��1440-1522�����µĄe������Αc����(1797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h�f־������•�[���d��“�Ǿ]�ִ��Ե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Ϫ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՝O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У��ԔM�՝���̖���h��ʿ��”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[”���˅��˕r������“�U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棨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ԣ���“�O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ˮ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̎��Αc���꡶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h�f־����ĩ•���^��ӛ��“ˮ���֣��ڿh�����eʯͤ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˄e�I����ʯͤ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١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ÿ�^�GϪ���mԢ춴ˡ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ѳ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Ğ�ɮ�ᡣ”���ϲ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˞�ʲ�N������h�ǎ�ʮ�e��ɽ�eȥ�x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Ѕ��˵ķ��ᣨ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ԅ����ڴ�ɽ�x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ɽ�W�Ɖ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ɰ����ʼ�ߣ�
�f����ɰ���Ą�ʼ����ȻҪՄ����ɰ�յ���Դ����Ŀǰ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ЃɷN�^�c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δ���Դ�f���ڶ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f���҂����Ҳ�Փ��ɰ�վ�����Դ춺Εr�������ݲ�֮�õ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ӛ�d���d��ɰ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īI——��ĩ�ܸ���ġ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зQ��“�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м����ˎ�ƈF������h�^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y�a���}ԥ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գ��ֽ����h�^ǰ��̎Ҳ��”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s����絝ʮ����(1644)���ɴ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ļξ���ʮ����(1544)���@�c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м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ξ�ʮ����(1533)�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ڕr�g�ϻ����Ǻϡ�Ҳ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ǰ��”����跽ʽ�^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˸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ξ��м��ᣨ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d��ɰ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ǰ��”���и��M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跽ʽ����赽�ݲ�ĸ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�赽�ݲ�ĸ��M���@���g���~��_��ȡ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ɰ���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u�M���^�̡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d��ɰ���Ą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ξ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N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ᵽ��“��ɮ”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Ҳ���Ǻϣ����ԛ_���~��֮�õ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ξ����g��ǰ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f���ǣ���ɳ����ɮ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չ����e�W�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ɉأ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W����ɮ�Ɖ؏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÷���f���ǹ���Ҋ���ص��չ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Ѕ������Ɖ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K�]���ᵽ��ɮ���H�ڡ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ע��ӛ�У�“�r�Ю�ɮ�@�״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Tɽ��ָʾ�����գ�‘�u���F��’���ˮ�֮���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ء�”���@�c�ܸ����ڡ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ӛ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f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݄t�f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ɮ�݄��Ɖأ�ɮ��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ɰ�����l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һ�����(1654)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ģ����r�Ӵ����ݵľ��Dž�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ס�˽�һ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÷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ĵ���ɰˇ���M��Ԕ���Ľ�Մ��̽�L���H���^����ɰˇ�˵��u���͟����^�̡��p���ɰ���˵IJ�Ʒ�ȣ��K���ܸ����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d��ɰ�����P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d�N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ġ�Ҳ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ɮ�݄��Ɖأ��_ʼֻ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ݲ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Kʹ��l�P����ǏĹ����_ʼ���ɴ�ʹ��ɰ�����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衣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“�U���F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~��ؕ”���t�ʹ跽�����˸�׃�Ͷ��ӻ����Kʹ���ɢ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@��һ����ʢ�a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ƾõĵط������Ϯ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Ӱ푺ͅ��˵ą��c�����ݲ�֮�ö����Ƶ���ɰ����߶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Ą�ʼ�߾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
�ߡ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Ŀǰ���е��Y�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]�г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،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^��˽���ղ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Ѓɰѣ�һ��“��`��”���ر����Ї��vʷ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飺�Ї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“����A�҉�”������۲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ɉ؞�����ɰ�D䛻������䛽�B�^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٘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ɉ؞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飺һ�Ǽ�ˇ�������Ɖؕr��ˇ�K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˃ɉص��u����ˇ��ʮ�ּ��죻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˃ɉ����ϵļ�ā�̶ȣ��ǹ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_���ģ����|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r��ȥ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ǿ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䓵��̿�������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ҕr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Ո�˕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֡��Լ��̿����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ˋ����ϵ��Ŀ̿������`�ء����Y�¿�����Ҳ�c�ī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ǟ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r�ډ��Ƿ��ڸ�һ��ͬ�G���죬߀δ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ԜI��(1533�˃ɉ�ȫ��δҊ�ԜI’�����b��ϻ���П��ɵģ����DZ��^���˃ɉ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ξ�ʮ����(1533)�ǽ�Ĺ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ؼ����f�v�r���ر��^���乤ˇǰ�ߣ��ɉ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M���C�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ɉؿ϶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“��`��”�c“����A�҉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20���o20-30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¹��L���r���£����r“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ɰ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Ƹ�Ϻ�’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M�о��ķ��u�����Ƴ��y�ԽyӋ�ķ����ҿ���Ʒ���@Щ��Ʒ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ʘO�ߣ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մɌ��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ɉ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кܸ��ղr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㽭����(����d)����Ԫ��(1864-1949)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“÷���h���”һ�ߣ���ɢʧ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̓�S����䛡��屾�������؈D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’ƽ�w’���漰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N��÷֦�w�x��ö���ص��п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֣��ظ�7.1��ס���13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飬�ˉؘO�п����Ǖr���ķ��uƷ����ԓ��ֻ���؈D��δҊ�似ˇ�����|�ȣ��m�ɷ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o���ж��Ƿ�_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¡�
���о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wɰ�؈D����ӛ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ղؼң��b�p���Ԫ��(1525—1590���ġ���Ϛv�����ɈD�V�����d䛃ɰ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F�ڿ����ġ���Ϛv�����ɈD�V���汾��Ҫ��1931���ɱ����z�S������棨�����Уע�����_ɭ��ӆ���ġ�Уע��Ϛv�����ɈD�V������ԭ�Ğ飺
“�����d�G׃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d�G׃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֪�η£��ߵʹ�С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dһ�G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R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d��Ҳ���Դ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иG׃�ߣ���ˉ��ߣ�����ɫҲ���A��֮�ᣬ�tͨ��׃�ɱ�ɫ���Üһ�֣��tһ��߀�ɺ�ɫ�ӡ������꣬�tͨ���}�ɺ�ɫ�ӡ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أ���¶���g���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t���أ��̳�֮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һҊ춾��ڽ����Ӽң��K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ٽ�ُȥ녡�
�����d�G׃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d�G׃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֪�η£��ߵʹ�С��D�����A��׃ɫ֮���Ѿ�ǰ�f��Ɲ����٘�ӡ�����Q֮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N֮δ���ߣ����Nδ��ĿҊҲ����Ҋ�˶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֮�ӡ�”��“�����d�G׃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}�ἰ“�tͨ���}�ɺ�ɫ��”��քe�й����(1879-1942)��Уע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r�ˣ����d���Uɽ֮��ͯҲ���S�Uɽ�x����ɳ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ɮ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䷨���칤�Ɖأ��Դ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؞�ɳ̥���֟o�|������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ɸ����V��”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þÄt��n��A���ԬF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ǸG׃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ͨ���D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Ʋ����顣”����wɰ�؈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d���а��Z녣�“ע��׃ɫ֮�f���ƌ��R�|Ұ�Z���ط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C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Ҋ�������֮녠���”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׃ɫ��”���҂����Ҳ�Փ�˃ɉ��Ƿ�“׃ɫ”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��d��D�V�ă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ȣ��W���J�顶��Ϛv�����ɈD�V���ǂ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һ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Ї��M�п��ŵķ����|���W�߽в�ϣ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1936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W����32���ϰl���ˡ��v�����ɈD�V��ο���һ�ģ�����1942���ڡ��Ї��W��2��2�ڰl���˴��ĵ��g�ġ���ϣ�Ϳb�ܵ�Փ���c�о��YՓ�����˟o���q�g���J��Ε��Ļ��A���δ��ġ����ňD���͡����ňD������۸ĵ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Y�ρ�Դ�t�ǡ��B�d���ň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Փ���ȣ��M���M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W�g��ķe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ɻ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J���˕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Εr�g��17���o���~��ĩ�ڣ��s1650-1699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Ȼ����Ϛv�����ɈD�V���ǂΕ������N�D�V�еă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Ҳ�І��}�ˣ������ڕr�g���@�ɰщؑ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Εr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У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��HҊ������d䛈D�V�ăɉ����ֺ͉؈D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Ҋ߀�ǂΕ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ӛ�d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Ѳ��ö�֪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1551-1631)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(1608)ǰ���ġ���{����ӛ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Ơt���ң���……�L��һ�����أ�Ħ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֮�Ⱦ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녣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ѳ�ᡣ"��Ҋ���Ž�D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@�ѹ�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Ҋ���ĸ���ǰ���ˉؿ��֮����
֮�������(1597-1689)�ڡ����Q�ļ������s1654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ӛ�Ѓɗl��ģ�һ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l녣�“�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ˉ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ʹ���ð�J����Ҳ���ң�”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”�l녣�“�T��䣬�M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”�Kע��“�����ղأ��༚���棬����ȝ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ǰ�l��oԔ�dԓ�ص����ƣ�ʹ�҂��o��Ҋ�乣�ţ���l����̨��̨�K�����Dz�K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K�Ƿ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ɡ�
߀������÷���ڡ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Ќ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A�����裬�w�Կ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Թ���ʽ��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̽�ӡ����”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У������ء�ӡ���ء��̽�ӡ���ء�
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u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磺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ڴ��ղؼ҅Ǻ�ԣ��1598һ�s1648������Ҋ�^�r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Еr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�ߣ�һ����۲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ղأ��ص�“���¹���ʽ”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ؑc�в����^�أ��ص�“�ɕѱ���¹����ƴ��”�߀����ĩ�Ɖ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”��ѣ��ˉ������ѳɞ鮔����ɰˇ�˷��u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Ҫ�ӱ�֮һ��
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��愓ʼ�ߣ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δҊ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“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”���Ɖؼ�ˇ��ͨ�^�r���ą���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չ�ˇʷ��ӛ�d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�ĵ�λ�Dz����ӓu�ġ�